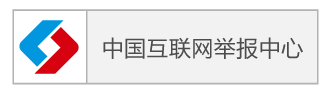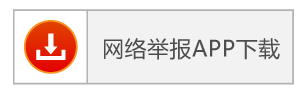A股再无600466.SH
而在黄其森之后,早年间兜兜转转才扎进房地产行业的蓝光发展创始人杨铿,也面临着同样的遗憾。
从进军房地产行业,到成为2023年首家A股强制退市房企,蓝光发展用了31年;而从偏居一隅的地方房企到成功登陆资本市场,蓝光发展用了8年;但从盛极一时的“四川房企一哥”到如今的落寞告别徒留一地鸡毛,蓝光发展仅用了3年。
在成都核心商圈春熙路上,一栋打造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26层高楼——蓝光大厦(曾用名“兰光大厦”)如今依然屹立,这是杨铿打造的第一个地产作品。彼时,成都二环路尚在建设,26层的高度足以俯瞰这座正在新兴发展的城市,蓝光发展借此打开了商业地产的大门,玉林生活广场、蓝色加勒比、香槟广场等,都是其开发的标杆商业项目。
创立10年后的2002年,蓝光发展开始进军住宅领域,并开发了首个住宅项目成都御府花园。在当年在四川省第一宗国有土地拍卖会现场,蓝光发展一举斩获两宗地;次年,蓝光发展又在成都国土局出让的21宗土地中拿下8宗。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是杨铿多次引用的一句话,这种理念,也深植在蓝光发展的基因里。
在高周转还未开始盛行的2009年,成都蓝光花满庭项目从拿地到首次开盘只用了57天,创下了当时的最快开盘纪录。此后,蓝光发展一路高歌猛进,成为川派房企的领军者。
然而,蓝光发展的欲望并不局限于成都。2008年和2010年,蓝光发展先后在重庆、北京拿地,开始布局全国。2015年4月16日,蓝光发展在A股借壳迪康药业上市,股价一度达到13.56元/股,而彼时其销售额尚不及200亿元。
需要注意的是,早在2013年,杨铿就提出“九年破千亿”的目标,并走上了“高增长、高杠杆”的快速发展之路。上市后的蓝光为了规模的快速扩张,更为坚定地奉行“3461”高周转模式,即拿地后3个月内开工,4个月开盘,开盘当日销售率达到60%,1年内实现项目正现金流。
上市仅4年后,蓝光发展就成功跻身千亿房企阵营,2019年销售额达1015亿元,较上市之初翻了5倍,这一年,杨铿在福布斯中国400强富豪榜的排名升至第296位。
也是在这一年9月,蓝光发展在上海设立总部,形成“上海+成都”双总部发展格局;10月,蓝光发展旗下物业公司蓝光嘉宝服务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形成了“A+H股”的双资本平台。蓝光发展迎来巅峰时刻。
然而,谁能料到,千亿神话的覆灭只在顷刻之间。
2020年,蓝光土地投资计划总额不超过400亿元,但实际上当年获取土地60宗,拿地金额达526.6亿元。随着当年“三道红线”政策出台,蓝光发展的财务状况已持续恶化,年报显示,2020年末蓝光发展资产负债率为82.04%。
同花顺财经显示,2020年10月,蓝光发展在广东佛山里水项目中,因管理与沟通问题,未与平安旗下公司达成一致的还款时间,进入平安银行的黑名单,成为债务危机爆发的前兆。
在强大的债务压力下,蓝光发展推进保交楼、与金融机构洽谈、制定化债方案、“精兵简政”等工作,却并没有实质性进展。为化解债务危机,不得已之下,蓝光发展选择出售资产,2020年9月将迪康药业全部股权以9亿元转让;2021年又折价卖了蓝光嘉宝服务与土储项目,获得数十亿元。
这对于总体债务超百亿元的蓝光发展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随着债务危机的显露,为隔离风险,杨铿辞去蓝光发展董事长职务,杨武正接任董事长,一个月后又兼任总裁;杨铿还将其所持蓝光发展全部股份转移到蓝光集团,作彻底切割。
但这并未能阻止危机的爆发。2021年7月12日,蓝光发展首次出现公开市场债券违约。尽管此后一度传出有万科、融创、华润以及四川省的部分国有企业洽谈合作,但均无实质性结果。
虽然杨武正曾坚定地表示“不会转让股权,不会甩卖公司”,但在债务违约压力之下,这些承诺显然无法兑现。蓝光发展及其控股股东的股票自2021年开始就被轮番摆上了拍卖席。截至2023年4月22日,蓝光集团持有蓝光发展3.56亿股,占比为11.72%,除了质押外,其余均处于冻结中,后续拍卖将可能导致蓝光发展控股权的变更。而在2021年年末时,蓝光集团持有蓝光发展的股份比重还在50%以上。
与此同时,蓝光发展的债务状况仍在持续恶化。2022年,蓝光发展的合同销售金额不足50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249.41亿元;总资产约1323亿元,同比减少24.21%;净资产约-238.69亿元,同比减少1858.96%。截至今年5月15日,蓝光发展累计到期未偿还债务本息合计425.56亿元。
从正式爆发债务危机到如今退市,近两年时间里,对于债务问题,蓝光发展一直未能拿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就算是在股价连续多日低于1元的情况下,蓝光发展也在未公开市场做出任何努力来提升市场信心。
在蓝光发展2023年家书中,杨武正曾说:“2023年我们会面临更艰巨的挑战,但是勇气与光芒会伴随在身旁。怀揣勇气与光芒,一起去翻越每座高山。”
如今,蓝光发展已从A股退市。根据蓝光发展公告,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所有股票将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依托主板券商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设立并代为管理的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板块挂牌转让。“预计可转让时间大概为8月10日,具体要看公告。”
面对商海的瞬息万变以及蓝光发展的应对之道,杨铿曾说:“我们尽可能找到一丝丝引路的光,在黑暗中摸索这头未知的大象。”如今,蓝光发展这头大象,是否还能等来那一丝光亮,以引导它走出黑暗、重回资本市场?
如今,等候宣判退市时间的不只泰禾。
中指研究院报告指出,目前,A+H股中有35家上市民营房企逼近退市(A股14家+H股21家),其中9家房企基本锁定退市。
房企退市对房地产行业、股东、员工和合作伙伴都会带来不良影响。目前,A+H股中上市房企数量高峰已过,未来上市房企进入、退出股市的流动将更强。部分企业退市,行业加快出清,也为其他房企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空间。[1]
截至目前,A股总共有154只ST股,其中地产类占了20只,占比高达13%。除蓝光发展已退市外,6月15日,*ST中天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被深交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不进入退市整理期,其股票将于深交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后15个交易日内摘牌。
此外,*ST宋都、ST粤泰、*ST海投、ST美置、ST泰禾、ST阳光城、*ST嘉凯均已触发终止上市条件而停牌。在停牌后的15个交易日内,根据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交易所将作出是否终止上述7家房企上市的决定。
截至6月26日收盘,A股共有12家房企的股价低于2元/股,其中泛海控股已经连续12个交易日低于1元/股,可能触发终止上市条件。而其余股价高于1元的企业中,也有部分企业的股价此前曾经跌至1元左右,随时可能面临退市风险。
“2021年下半年开始,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调整阶段,高杠杆企业风险不断暴露,数十家民营房企发生债务违约,行业进入加速优胜劣汰阶段。触发退市风险警示的房企多数是出险房企,上市公司退市对公司融资、销售等经营活动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刘水向每经头条记者分析指出,A股房企的“戴帽”原因,主要是涉及上市公司“退市及风险警示”条款,集中在“财务类强制退市”警示、“其他风险警示”警示的条例。从行业竞争格局看,优胜劣汰机制将助推房地产行业股市表现分化加剧。当前房企由于经营亏损以及债务违约等多种因素叠加,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企业迅速增加。
面对即将到来的退市危机,部分房企选择了奋力一搏,股东增持成为了最常见的护盘举措。
以金科股份为例,5月下旬开始,金科股价持续下挫,逼近退市的1元面值。对此,金科股份宣布了控股股东的增持计划,即金科控股将在6个月内增持金额5000万元到1亿元的金科股份的股份,增持价格不高于1.5元/股。此后,包括金科股份董事长周达、总裁杨程钧等在内的18名董监高及核心骨干也宣布,在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500万元到1000万元,且增持价格不设上限。
5月24日,金科股份收盘价首次跌破1元面值,而当日金科股份就宣布,金科控股指定财聚投资增持金科股份。5月26日,金科股份终于在股价触及跌停、最低报0.77元后罕见上演“地天板”,收盘价来到0.95元。6月2日、5日、6日,金科股份三个交易日收获两个涨停,股价来到1.07元,重回1元上方,随即宣布停牌谋划资产重组。最终,金科股份8个交易日累计大涨39%,回到安全线。
暂时转危为安的还有*ST新联。6月8日,*ST新联上涨4.82%,收盘价格为1.74元/股,较2023年5月19日的收盘价0.97元/股涨幅达79.38%。而在前一日,*ST新联公告称,控股股东新华联控股于5月25日-6月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逾3793万股,增持股份比例已达公司总股本的2%。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重回1元线于房企而言并非意味着警报解除。
如*ST泛海,原本其股价已连续15个交易日低于1元,在不断涨停拉升后股价于5月11日收于1.01元/股,之后再度走低跌破1元。5月底,*ST泛海股价连续涨停拉升但股价仍不足1元,5月31日收于1元之下,已经连续14个交易日不足1元,退市警报再度拉响。但在6月2日,*ST泛海股价再次回到1元以上,6月7日再次跌回1元以下,6月26日的收盘价为0.96元/股,已经连续12个交易日低于1元/股。
而此前,泛海控股的控股股东已在5月11日-6月2日完成增持约8912万股,截至6月2日已经增持了8476万元,完成了此前的增持计划。在该项增持计划完成后,6月3日,泛海控股再度公告称,控股股东自6月5日起3个月内再拟以5000万元-1亿元增持公司股票。
在刘水看来,“这些救市措施如大股东增持、装入优质资产,短期对提升公司股票价值有帮助,避免了股票价格快速下跌。长期来看,公司要尽快完成债务重组、盘活存量保交楼、加快销售回款,尽快恢复经营,才能避免退市发生。”
狂飙的苦果
复盘近期面临退市危机的房企,它们都有着一条相似的发展轨迹——激进扩张,高溢价拿地,冲击千亿规模,但最终被高负债反噬。
如蓝光发展,2019-2020年,蓝光发展分别实现营收391.94亿元和429.57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4.59亿元和33.02亿元;同期偿还债务支付现金分别为385.46亿元和381.06亿元,严重吞噬利润。
而在2018年底,万科已经高喊“活下去”时,蓝光发展当年的拿地数量却达到创纪录的85宗。此后的2019年和2020年,蓝光发展的拿地数量分别为48宗和60宗,其中2020年溢价率超过50%的地块就有21宗。
再看已于6月12日停牌的ST阳光城。
2016年阳光城定下了“3+1+X”的扩张策略,开始向二、三线城市进军,然后又通过招拍挂、收并购、一级整理、三旧改造、产城融合等多方式获取优质土地,土储规模不断增长。凭借着这一激进的运作手法,阳光城在2016-2018年连续3年保持着50%以上的销售额增速,2018年实现销售额1628.56亿元,跻身千亿房企阵营。2019年,阳光城继续保持29.58%的增速,全年销售额达2110.31亿元,迈入2000亿级别,跻身中国房企销售额TOP15。
不过,“狂飙”突进不仅为阳光城带来了千亿业绩规模,也带来了高负债、资金吃紧的隐患。2018年,阳光城的总负债超过了2000亿元,截至2022年末,这一总负债规模达到了2746亿元,其中流动负债高达2530亿元,短期借款为40.94亿元,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为290.5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542.1亿元,三者合计达到了873.54亿元。而同期,阳光城的货币资金仅为83.49亿元。
然而,在房企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融资方面,尽管2022年底房企融资放开,融资端“三支箭”开闸曾使房企股价大幅上涨,但出险房企并未受益。
2022年,ST阳光城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为7.97亿元,2023年一季度低至1.79亿元,而2021年则有377.2亿元。2021年,*ST蓝光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147.55亿元,2022年断崖式下跌至5.04亿元,今年一季度为0元。
即使没有在退市边缘挣扎的房企,信用较弱的民营房企的融资状况也没有明显好转。
克而瑞统计显示,5月80家典型房企的融资总量为263.29亿元,环比减少56.4%,同比减少60.4%,创下了2020年以来单月融资的新低。其中,房企债券发行了178.46亿元,环比减少49.3%,同比减少59.8%。而发债企业仍以招商蛇口、金融街、保利等国企央企为主。[2]
克而瑞分析指出,虽然融资环境有所优化,但是短期内仅能惠及白名单优质企业,部分财务困难的房企仍较难获得支持,因此未来仍可能有更多房企曝出债务违约事件。再加上当前房地产销售仍未全面复苏,房企的流动性问题仍需要行业注意。